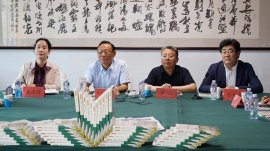背上是几十斤重的树苗,脚下是陡峭的山坡,手脚并用往上爬,生怕一脚踩不稳连苗带人滚下坡……
午间,靠在客厅沙发上打了个盹儿,83岁的董鸿儒又梦到了苏木山。这个他为之倾注一辈子心血的地方,曾无数次地出现在梦境里。
“我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种树;一辈子只呆过一个地方,就是苏木山。”老人抬眼看向客厅墙壁上方挂着的苏木山的照片,被树苗压弯的脊背弓成一座小山。
42年,15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在荒芜的山脊上种满绿色和希望,用青春和汗水写下了青山不老的传说。
一座山,因他而变
苏木山,山连着山,坡连着坡。“山大沟深石头多,一出门就爬坡”是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形容苏木山的顺口溜。
1958年10月,20岁的董鸿儒被派往苏木山护林站当护林员,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早晨背着行李出发,傍晚时终于爬到了挂在半山腰的护林站。
“护林站只是一间低矮漏风的土坯房,两面悬崖峭壁,出门、回家都要爬坡过坎。屋里只有一盘土炕、一个锅台和几件简单残破的炊事用具。说是来当护林员,可只是一片荒山秃岭。”尽管来的时候做足了心理准备,可看到眼前的景象,董鸿儒的心还是沉了又沉。
那一夜,听着附近村里老狗的狂吠和怒号的风声,他一夜无眠。
走,还是留?
迷茫之际,村里一名叫李德库的老人给他讲述了解放战争中老一辈革命者在苏木山坚持打游击的往事。“当年游击队员出生入死、爬山卧雪坚持跟敌人作斗争,那才叫艰苦、危险哩!”李德库老人的话,让董鸿儒豁然开朗。
“我12岁就成了孤儿,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今天的我,现在正是党需要我的时候,我怎么能退缩!老一辈革命者为了保卫家园在这里英勇战斗,我为什么不能!”这一留,就是42年。
留下就要干出一番事业。1959年夏天,董鸿儒带着一个熟悉苏木山地形的民工开始上山调查。三个月早出晚归,爬遍了苏木山的沟沟坎坎,穿坏了2双鞋子,他边走边做记录: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春秋刮风黄沙起,雨季洪水冲走牛,人无树遮阴,鸟无树搭巢……
更让他坐立难安的是,苏木山距首都北京仅200多公里,如果水土继续流失下去,永定河上游的生态必然遭到破坏,进而影响到北京的生态安全。
“不对!苏木山需要的不是护林,而是种树!”实地调研后他作出清醒的判断。
董鸿儒迅速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建议苏木山尽快成立国营林场,植树造林、恢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上级部门重视。1960年春,自治区正式批准成立苏木山林场。
一座山,因他而绿
建林场,最缺的是人。县里物色了很多人选,但他们都以各种理由回绝了。董鸿儒好不容易盼来了场长赵守礼,两人徒步走出山外,亲自去周边的生产队雇回几十个工人,开始边建场边种树。
3个月,董鸿儒和工人们起早贪黑,平整场地筑根基,挑水和泥脱土坯,19间场房拔地而起。
植树造林山高坡陡,机器上不去,董鸿儒将几十斤浸湿的树苗用麻袋捆好后绑在肩上,弓着身子手脚并用往上爬,工人们学着他的样子也往上爬。饿了啃几口窝头,渴了喝几口山泉水,怕苗木干了影响成活率,大家都不敢歇息。
10多里的山路,一天要往返三四次。双肩勒出了血,血肉和衣服粘在一起,脱的时候生疼。手上磨起了水泡,吃饭时连碗都端不稳;干一天活儿挣的工钱只够买3两莜面,大家吃不饱饭,野菜、蘑菇、野谷子……山上能吃的都吃了个遍。
为了能吃饱饭,董鸿儒春季带着大家在附近山沟里开垦荒地种粮食,冬闲季节带着工人上山割柠条编织筐子、篓子换钱改善生活。可即便如此,冬天还没过完,工人就走了一半。
“这样下去不行呀!”为稳定人心,他跑回家说动妻子,带头将家搬到了苏木山。晚上睡觉,将家里能盖的东西全部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哆嗦;早晨起来,前夜锅里的水结成了冰坨。
敌不过这恶劣的环境,在已经失去一个孩子的情况下,董鸿儒第二、第三个孩子接连染上痢疾。山上缺医少药,去县城的医院要走两天,两个孩子来不及送医就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离开这里吧!去条件好的地方工作。”妻子悲痛欲绝的哭诉仿佛就在耳边,董鸿儒的泪水夺眶而出。“不能走啊,山还没有绿,如果就这样放弃了,我们怎么向党交代,怎么向死去的儿女交代!”
隐忍着痛楚,他给第四、第五个孩子分别取名存战和存在,希望孩子们能存活下来。
“他永远把种树放在第一位,事事都带头冲到前面。”跟他一起在林场工作过的老人陈关荣说。妻子生病住院,他怕耽误造林一次都没去看过;刚做完痔疮手术,工人们劝他回家休息,可他直接扛着工具就上了山;闲暇时大家聚在一起下棋、打扑克,只有他抱着一本书埋头苦读。
造林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缺乏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经验,连续3年造林都以失败告终,县里传出撤销苏木山林场的消息。
事业还没开始就要夭折,董鸿儒和赵守礼心急如焚,去县里求情。“再给三年时间,我们一定找出适合苏木山的树种!”被两人的执着所感动,县里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听说河北有个林场跟苏木山自然环境差不多,种植华北落叶松成功了,他们一刻也没耽搁前去考察,并想办法买来种子进行育苗。
1965年春,林场背水一战。成功,林场就能留下来;失败,就只能下马。播种、覆土、浇水、除草,严格按技术要求操作后,大家没日没夜守着苗圃,看到啄食幼苗的鸟儿立刻赶走,遇到高温天气随时喷水降温。当年9月份,精心培育的树苗根系发达、苗茎粗壮,苏木山林场华北落叶松育苗成功了!
正值秋季造林,大家趁热打铁将树苗种进去。第二年春天,人们小心翼翼扒开苗木越冬土,绿油油、齐刷刷的小树苗冒了出来。“活了!”“成了!”董鸿儒和工人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说到激动处,董鸿儒起身,挪动着被关节炎折磨的双腿,到窗前的资料箱里取出他的两个宝贝:《造林技术》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泛黄的书页曾激励陪伴了他一个又一个苦熬的夜晚。“那时候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一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谁说苏木山栽不活树!华北落叶松育苗造林大获成功,填补了我区西部地区落叶松造林的空白,苏木山林场造林经验被广泛推广。
绿色迅速蔓延,董鸿儒的名字被更多人知晓。上世纪80年代初,组织要提拔他为县林业局副局长,工资有保证、待遇高,孩子们上学、就医也方便,他干了几天放不下苏木山,又跑了回来。1994年,他全票当选县政协副主席,他提出不要办公室、不领工资,只要继续留在苏木山。
“饥饿苦寒,我没有想过离开;痛失三子,我没有想过离开;现在,我更不会离开。”问他为什么,他说,绿化荒山是他入党时许下的诺言,也是他毕生追求的使命。
像是冥冥之中有天意,董鸿儒的儿子董存战也回到苏木山工作,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
一座山,因他而兴
“你看,最早种下的树现在我都抱不住了。”老人摩挲着自己秋天再上苏木山时拍的照片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经过不懈奋斗,苏木山林场从1个林区发展到5个林区,3000多万棵落叶松绿满山坡,森林覆盖率达到74.8%,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林场。据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专家测算,苏木山林场的森林资源每年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固碳释氧、森林游憩等方面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高达2.67亿元。
“自从建起林场,再也不发洪水、不刮沙尘暴了,也不用再担心洪水冲走牛羊、冲毁庄稼。”苏木山脚下,卢家营子村90多岁的老农民李生和说。
“一到旅游季节,村里年轻劳动力都上苏木山打工,土鸡、杂粮、山蘑菇供不应求,人均收入从三四千上升到一万五。”卢家营子村党支部书记许青说,前人栽好树,我们就得把树保护好、利用好,为百姓造福。
外出打工的李美桃回乡创业,开起了“常新宽农家乐”,收入翻了好几番。
……
“这一辈子,能为人民做些事,值了。”董鸿儒特别满足。
苏木山还流传着很多和董鸿儒有关的温暖记忆。
上世纪80年代,苏木山林场学校的教室仍是库房和棚圈改造的,条件艰苦没有公办老师愿意来,董鸿儒找到教育局批了地、盖起了新校舍,还要来了老师,解决了附近村庄的孩子们上初中、高中的难题。从建校到1999年董鸿儒退休,学校共走出20多个大学生。
曾经,苏木山没有电,孩子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学习,打个电话要走一天,报纸一个月才送一次,看不上电视,文化娱乐生活一片空白。在董鸿儒的提议和奔走下,林场出资为周边4个村子拉上了电。村民们听上了广播、看上了电视、用上了电灯,孩子们看书写字再不用担心煤油灯燎了头发。
林场职工杨吉因病去世,留下一个12岁的孩子无人照顾。董鸿儒说,苏木山的孩子,得苏木山来养。他将孩子接到林场,照顾他生活起居,供他读书、送他当兵,如今孩子已经成家立业,把董鸿儒当成了自己的父亲;职工吕文喜得了肝硬化,董鸿儒带着他去张家口看病,一直照顾他到去世……
退休后,董鸿儒在兴和县城关镇南关村建起了苗圃,一直干到72岁,又让500亩荒滩变成了绿洲。
时至今日,老人家里茶几的透明塑料布下,仍压着一张记满护林员电话的纸,那是他的不舍和牵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董鸿儒用一辈子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青山不言,绿色为证。粗壮的落叶松笔直地伸向天空,阵阵松涛回响在山间,鸟儿鸣叫盘旋着飞向远方,诉说着苏木山的山河巨变。(霍晓庆 包荭)